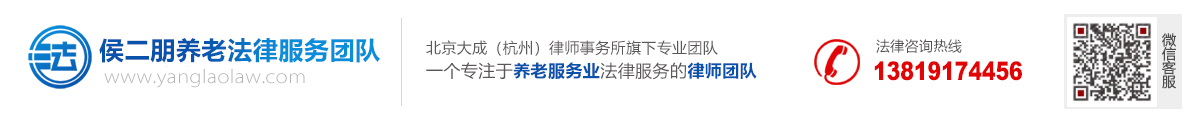
从第一个岗位——福利院里的“收住”,到后来徐汇区社会福利院副院长,徐汇区第二社会福利院书记、院长,一路摸爬滚打,他形容这个职业:极其繁杂、压力极大、问责极多、褒奖极少、福报极大。
在姚威看来,2020年和2022年两波疫情让养老人、养老机构从默默无闻一下子成为了社会热点,同时也成了“高危”,但养老人的苦和难绝不是这四个月才有,他们承受的压力看不见摸不着,因此很难被“同理”,而更多更复杂的社会情绪和认知主宰着每个人的判断与评价。“这是一份工作,但是一份需要更多情怀和爱心才能坚持与支撑的工作,我们不一定完美,但一定做到问心无愧。”与其说是告白,不如说是一句勇敢的承诺。
在上海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日常监测的500家机构中,姚威此前供职的“二福院”曾获得全市第一,而徐汇区已连续数年总分排名全市第一。这波疫情中,徐汇区社会福利院、徐汇区第二社会福利院两家公建公营机构无一例老人感染,这背后养老人不为人知的努力或许正是姚威的底气所在。“倾听那些听得见弱势群体呻吟的人的微弱声音,看见那些看得见弱势群体表情的人的朴实表情,期望这种‘看见’能化为真正的‘改善’!”
以下是他的口述实录。
我是2001年“二福院”开张时进入这个体系的,30岁不到,一点不晓得养老是啥。还记得去“二福院”应聘,面试官、也是后来我的第一位领导问我,如果下班走出门口,正好看到一辆“120”进来,你会怎么做。我说返回工作岗位,和司机沟通,把老人送下来,可能的话陪去医院。完全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思考方式,很宽泛,很空洞,很不可操作,但表明了一个态度,我的态度是好的,我是随叫随到的,我是不计较的。我们这个行业就要求就是这种态度。
它始终是一个待命状态,不可能把边界划得很清楚,因为老人的状况是不可控的,他什么时候有需求,什么时候出问题了,是以他为中心,小到我们一家机构,小到一个具体岗位,他的服务原点都在老人身上。所有老人在养老领域的每一个共同点,我们会有一个团队。比如说心理支持、社会活动、身体康复,饮食等等,各种团队对应老人的需求,他发出信号,我们会接收,我们也会主动去发现他的需求。
你说酸甜苦辣这个东西,它是互相交织的。每个阶段的苦不一样。我刚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那时的苦是手机24小时不能关机,半夜三更会忽然来电话,那时候我还在做“收住”,对老人家庭情况相对熟悉。民间有句话叫“八十不留夜”,它会发生不可预知的状况。机构里入住的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5岁,意外发生的频率可想而知,我就在这些意外发生后的第一类联系人里面。突发状况,老人的诉求、家属的诉求,随时扑过来。
比如说送120,打电话给家属,半夜三更没人接很正常,但120要找家属,医院要找家属,时间就是生命。没有家属的认可,直接把老人送医院行不行?行,但会有很多问题。如果经过抢救老人回来了,家属可能会感到庆幸,表示感谢,但如果没有抢救回来,家属可能会说为什么没通知到他们,没有让他们见到老人最后一面。
所以从程序上来说、从沟通上来说、从伦理上来说,我们都要通知到家属,能达成一个共识,电话是不能停的。现在八九十岁这代老人不少是多子女家庭,各有各的想法,有时情况紧急,我们把老人送医后经过一些简单处理,他安全回来了,某个家属可能会说,他没事你们折腾什么!120急救要花钱,上各种仪器检查要花钱,那在那个紧急状况下我们该怎么做,你能理解吗?
一个家庭一个老人发生这种情况,你说那天太忙了;当它集中在一起,成为你面对的常态的时候,就是一种苦,但这种苦还在自己可以调适承受的范围,更难的是背后的苦。送医的决定谁来做?如果沟通下来达成不送医再观察一下,这个决定是家属做、院长做,还是当时的总值班做?如果老人在观察期间发生状况,家属和旁观者可能会说,我不是专业的,我们不懂,你们是专业的啊!
有的多子女家庭如果有个老大做得了主,那还好;如果一个家属说,我定不了的,要去问问兄弟姐妹,那可能一圈电话打下来,该耽误的都耽误了。但是你没有授权,你不是监护人,如果这个过程中出现问题,家属、社会、领导、旁观者,他会怎么说,做了这么多年养老你都不懂吗!我懂,但又怎样呢,当所有这些日积月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活太苦、太不可诉说、太没有理由了。
有一个家庭,老人是我“调访”(调查家访)后进来的,入院时70多岁,老先生身体硬朗,在家里属于说一不二那种,6个子女中有在国外的,有技术人员,也有下岗的。子女来求助,说老人脾气大,他们从时间、精力、专业上很难满足他的需求,老人的脾气性格已经到了影响小家庭正常运转的那种程度。我去他家里看,和老先生聊了很多。他爱人不在了,子女联系过几家机构送他去,他不愿意,说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心理上抗拒入院。
后来家属说,我爸爸说你这个人蛮有趣的,没有反对,之前都是把人家骂出去的。我说好,我跟老人再确认。后来通过正常程序把老先生接进来了,因为他性格方面有些特殊,我又在“收住”岗位,所以比较关注他是不是适应新环境,没事就陪他聊聊天什么的,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子女,包括在国外的有时候也会说,我爸爸只有看到你会笑。后来,老人家身体慢慢走下坡路,我一直陪伴他走到最后,他在医院里过世了。他走的时候,我已经是“二福院”的副院长,十多年的时间跨度。
没想到这件事后,他的一个子女跑到我这边来,说老人进来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怎么就没了?后来我慢慢了解因为家里要分遗产,扣除成本,他可能是条件最差的一个,他觉得老爷子最后住院了,福利院里的床位费就该退出来,这个成本应该省掉。那老先生如果没有去世,进了医院,这个床位我们要不要给他保留呢?这种情况在老人晚年会发生很多次,合约里也注明只保留床位的费用,护理、伙食等没有发生的都不算,我们的打算不是老人过世,是他治疗结束后正常回来啊!
那天老人的6个子女都来了,他拿起我桌上的电话要砸过来。他说,我父亲在天上看着,会朝你吐口水。我说我就讲两句话,第一,你父亲在天上看着我会笑,会骂你;第二句,你父亲进来十几年,你进过我们院门几次,如果要吐口水,不是对我。我说你在国外的哥哥姐姐,你在上海的哥哥,你们所有人加起来得到的微笑,还不如你老父亲平时对我的,他吃什么药你知道吗?他有哪些病你知道吗?他喜欢吃什么你知道吗?鸦雀无声。那一刻我对人性,对老人有一种深深的悲哀。
这波疫情前,“一福院”和“二福院”两家机构大概的入住率在80%-90%,300多个老人,平均年龄87.6岁。疫情前,家属每天可以来院里看望老人,不少子女也是这么做的,有一对母子给我印象特别深。老人是一位母亲,入住很多年了,退休的儿子年纪也大了,每天早上过来陪她说话,做老人喜欢的事,中午回去吃个饭,下午又来,晚上回去吃个饭,再来,陪到七八点钟,然后我上楼,他正好回去,常常会碰到,几乎每天如此。天好的时候,他推着轮椅带老人在院子里逛,累了就坐下来,陪着说说话,甚至什么都不说,搂着母亲肩膀,我看着很感动。他说我反正在家里,离得又不远,就过来多陪陪她,其他专业的事有你们做。
他付出的其实比金钱多,我不说认同还是反对,但我非常羡慕这位母亲,能够有一个孩子给她这样的支持和陪伴,那个画面真的很温馨。这样的家庭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也会碰到,它也是支撑我坚持下去的一种力量。
如果你仔细想,每个家庭为什么会把老人送到机构,他一定是自己的生活过不下去了,他已经备受煎熬了,希望借助专业力量去化解去“减负”,机构就是这些老人和他们背后无数个家庭的容器,那这个容器里面的服务人员,他们的日日夜夜又承受了些什么?从3月9日养老机构封闭管理至今,养老人的每一天其实都过得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守护着区域内、机构里成千上万个老人,但他们的感受其实很少被社会听见、看见,即便被听见看见了,大家也会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对,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埋头做事肯担当的人不是傻,是心中还有热情,还有敬畏。
5月13日,我正在抗疫一线忙着,忽然收到一组我自己抖音号里的截图,仔细一看是我父亲发来的。那时我在单位封闭了50多天,因为听歌想家发了一组图文,80岁的老爸竟然就截了这几张图过来。那一刻我心揪了一下,原来平常少言寡语的父亲一直在关注我,竟然还下载抖音粉了我,在我脱离了他们熟悉的轨道,无法经常去看他们的时候。
这些年做养老,越来越深地体会到父母心。有一次在楼下聊天,说起工作忙不忙累不累,他们说了一句:你现在做养老,我们也放心了。那时候就觉得,有他们的认可,这么多年的辛苦都值了!我觉得作为子女最大的孝,是让父母有这种安定感、稳定感,这也是我们自己幸福的来源。
福利院里的很多时刻,迎春的喜庆市集,3000岁的留影,97岁老人和钢琴大师的联袂弹奏,老人由衷的笑,家属真心的赞,都是点点滴滴的甘甜回味。20多年做下来,我对这个行业的人和事有很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慢慢积攒的,我希望这个行业好,所有的处理和过程都是规范的、健康的,用制度设定一个底线,然后努力向上求人性,求温度。
我们这一行招人难、留人难,疫情后员工离职时有发生。疫情对整个行业可能是一次被迫的自我革命和自我精炼,能够顶下来的机构和人,以后再碰到什么,我想他都能扛住。坚持下来的都是铁粉,是真正的砥柱和稳定器。
所以你说酸甜苦辣,我想这是个调味,“咸”才是一个最基础的底味,养老人对这份良心工作的坚守,用最大的责任心、爱心、耐心守护这座城市最需要帮助、最弱势的群体,这是我们的“底味”。
希望这五味俱全的职业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希望这些最可爱最辛苦、给每一位长者带来宽慰笑容的人,能被更多的人珍惜和善待!
转载于公众号《 新华养老週刊》来源:新民晚报。
https://mp.weixin.qq.com/s/Ip8CFl-lrv96ADpXltkyPg(2022年10月23日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