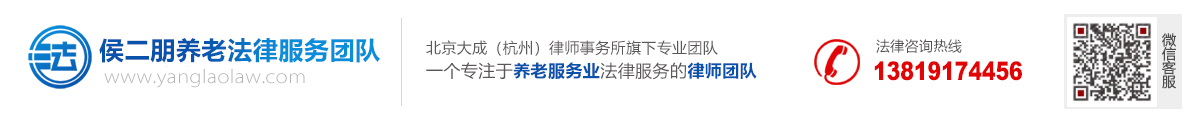
文献来源:睢素利.从伦理和法律视角探讨患者自主权在预先医疗决定中的实现[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7,30(10):1213-1218.
摘要
首先从保护患者自主权的角度出发,思考分析患者自主权在预先医疗决定中的实现问题。然后从法律规定中对个人自主权利的保护,以及从伦理原则中尊重人的自主性为基础,分析在我国推广、采用和落实预先医疗决定书的可行性。再次从法律对意定监护的认可角度探讨充分保护患者决策自主的路径,分析在我国目前法律框架内实行预指医疗代理的可行依据和可能涉及的相关问题。在上述基础上,提出为保护患者在医疗中的自主权需要有效地推广和应用预先医疗决定,以及采用预指医疗代理充分落实患者的医疗意愿,保护患者自主权在医疗实践中的实现。
医学技术的发展,使患者的生命在终末期可以得到维系和延长,而这样临终状态下生命的维持带给患者的可能是身体的痛苦和临终的折磨。实践中,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的特殊病况下是否需要采用维生手段或者其他医疗措施来延缓生命,需要患者个人依据自己的意愿谨慎地做出决定。个人在做出重大的医疗决定时,都会希望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如果已经没有能力表达意愿,那自己的真实想法也希望他人能够知晓并且得到尊重,这也是患者的自主权在医疗中的体现。 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患者的自主性,在医疗实践中出现了预先医疗决定(Advance Directive)。预先医疗决定使患者真实的医疗意愿能够在意识清楚时得到明确表达,可以说是患者自主权利的延伸,目的是患者在失去自主表达和做决定的能力后,依旧能够使人知晓其真实意愿。从保护患者自主权的根本利益出发,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通过立法明确了预先医疗决定的实践应用。我国目前对个人意思自治和个人自主权的保护也有了明显的进展,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权利不受干涉,尤其是《民法总则》规定了成年人意定监护,这将会促进我国预先医疗决定的发展推广和在医疗实践中的适用。本文从伦理原则中尊重人的自主性和法律规定中对个人自主权利的保护为基础,分析在我国采用预先医疗决定书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其现实可行性,同时提出在实践中应用预指医疗代理来保证充分落实患者的医疗意愿的实现。
1预先医疗决定的由来及应用
预先医疗决定的概念最早由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位律师提出。在1969年的一份法律期刊上,路易斯·库特纳律师提出可以参考财产法规定允许个人在生前对身故后的财产处理做好安排,也允许个人提前声明在自己无法自主表达个人意愿时想要得到的医疗要求,也就是个人在特殊病况下对其生存意愿(Living Will)的预先决定,这种预先决定也被称为生前预嘱[1]。1972年美国安乐死协会印制了第一份生存意愿书表格,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直到1976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自然死亡法。这是第一部通过预先医疗决定所表达的生存意愿合法化的法律,这部法律明确了临终患者有权拒绝使用维持生命设备。在美国,目前几乎每一个州都有类似的法律规定,其中很多都以简洁的语言描述了生存意愿书,这可以说是预先医疗决定最早的形式。但是实践中生存意愿书的内容通常都过于简单,为确保明确知晓意愿人的真实想法,促使逐渐产生预指医疗代理,宾夕法尼亚州在1983年最先以法律明确了预指医疗代理制度,实践中通常而言由患者的配偶、成年子女、成年兄弟姐妹或其他近亲属来担任患者的医疗代理人。其后美国国会在1990年通过了患者自决法案,该法案大力推广了预先医疗决定[2]。
在欧洲,1997年欧洲人权和生物医学公约首次规定预先医疗决定,对于预先医疗决定的制度规定欧洲各国也不尽相同。预先医疗决定在有些国家没有法律约束力,比如意大利、土耳其、法国、希腊等;而在比利时和德国则有很高的法律约束力。另外,对于预先医疗决定的时间效力方面,不同国家也有所不同,比如法国规定了必须每3年更新一次预先医疗决定书,并且指定预先医疗决定的代理人时必须由医生认可;而奥地利规定每5年更新一次,同时规定对于因为不符合规定而不具备直接法律约束力的预先医疗决定书,在实践中可以作为决定的参考;通常预先医疗决定有法律约束力,但在荷兰,当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时医生可以拒绝执行预先医疗决定书[3]。
在亚洲的国家和地区,预先医疗决定的适用范围不广但是也在逐渐发展中。新加坡在1996年制定并于1997年7月正式实施了《预先医疗指示法》,按照该法律规定,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有权提出不使用或撤除维持生命设备,但撤除或不使用的治疗不包括安宁疗护[4]。中国香港地区虽然没有明确预先医疗决定,但认定除非有人质疑,否则应该尊重患者预先医疗决定书表明的医疗意愿[5]。我国台湾地区在2002年出台了安宁缓和疗护相关规定,规定疾病终末期患者可以自愿选择只进行安宁疗护,但不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6]。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12月我国台湾地区颁布了病人自主权利有关规定,按照此法规定未来包括“末期病人、处于不可逆转昏迷状况、永久植物人状态、极重度失智与其他经公告疾病”的患者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医疗。该规定的宗旨就是保障病人在知悉自身病情的基础上自主选择自己后续的医疗方式,以期在医疗中实现病人的主体性,尊重病人的医疗自主,保障病人的善终权益。
目前我国大陆尚没有关于预先医疗决定的明确规定,但是实践中在一些公益机构和组织的倡导和推广下,预先医疗决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比如2011年成立的选择与尊严网站(网址:www.xzyzy.com)就提出临终时的急救措施和生命维持设备的使用加重和增加了患者的痛苦,患者身体完全被机器控制而缺乏生命尊严,同时临终使用维生技术需要投入巨大的医疗资源和社会资源,基于此,该网站倡议“临终不插管”,并且在网站上提供了拟写的生前预嘱的参考样本。倡导个人在身体健康或意识尚清楚时签署生前预嘱,表达自己在无法治愈的伤病终末期或临终状态时需要或不需要哪种医疗护理。另外,2013年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该协会致力于推广生前预嘱在实践中的应用,并提出总的嘱咐原则是:“如果自己因伤病导致身体处于‘不可逆转的昏迷状态’‘持续植物状态’或‘生命末期’,不管是用何种医疗措施,死亡的来临都不会超过6个月,而所有的生命支持治疗的作用只是在延长寿命而存活毫无质量时,希望可以停止救治。”可以说这一原则体现了对患者放弃治疗的自主决定权的尊重。
2人的自主性和医疗中患者的自主
尊重是伦理的基本原则。人之所以要被尊重,就在于人有理性、有意识、有意志和有信念。人具有自主权利的个体条件是人的灵魂和意志,因此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个人都应当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个人行为。尊重人首先就是要尊重她/他的自主性和自我决定权。自主性也就是个人拥有自我决定的权利。自主性也是一种理性的能力和自由,是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选择的计划决定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和自由,也正是自主性成就了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独特价值。
在医疗实践中,个人的自主性主要体现为患者的自主,即在医疗活动中患者具有独立和自愿的选择权和独立并且自愿做决定的权利。自主原则是医疗活动中的重要伦理原则,该原则要求医师在诊疗活动和诊疗过程中要尊重患者在理性地选择诊治决策时由他本人或代表他本人的亲属做最后的决定。自主有三个基本的特征:一是意愿性,是患者本身或有权代理其行为的人的意愿行为;二是目的性,是患者建立在理性考虑基础上对关注后果的选择;三是坚定性,它不是因为外界干扰而妥协的选择。自主原则的实质是对患者独立人格的尊重和对患者自主权利的保护。在医疗实践中,对患者有利和不伤害是基本的伦理原则,但只做到有利和不伤害还是不够的。在医疗中患者是医疗活动的目的,是医疗手段的承受者,也是医疗活动结果的承担者,无论医疗活动的结果是好是坏,或是利弊兼有,或是不可预测,都需要由患者来承担医疗的最终结果。这样的角色决定了患者有权对将要在其身体上所实施的诊疗方案做出自己的选择,尤其是对身体有一定侵害的诊疗措施。患者应该对是否采用这些医疗手段有自主做选择和决定的权利。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只有患者个人才最理解自己的最佳利益,也许这里的最佳利益在他人看来并不是最佳方案[7]。因此也只有患者个人才能够做出最符合自己最佳利益的医疗选择,所以医疗活动中应由患者本人做出符合自己意愿的医疗决定。医疗中患者的自主正是从根本上体现了患者的选择权。其实在医患治疗和被治疗的关系中,患者的选择权是其核心[8]。虽然患者需要医生给予诊疗,但是不管在法律还是伦理层面,通常情况下是由患者自主选择决定是否建立起这种关系。医疗中的自主原则从根本上表达了患者的自主选择的权利,也就是患者自主权。
患者的自主选择权是指患者在医疗中经过深思熟虑就有关自己的疾病和健康问题作出合乎理性的决定并据此采取负责的行动。强调患者自主权首先要承认患者有参与医疗过程的权利,并且承认医疗很多方面的决定应由患者自己来作出。对自主性的尊重要求医生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无论患者做出什么决定, 只要该决定是其基于理性做出的其认为是合理的决策, 即使某些决策是其家庭成员或者医生无法认可和接受的, 也应该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9]。对于疾病终末期的临终患者而言, 如果他们已经不愿意继续忍受疾病和医疗干预的痛苦, 认为放弃对自己的治疗是符合其最佳利益的选择, 那么他的选择也应该得到尊重。尊重自主权除了被用来拒绝医疗中的家长主义做法外,在实践中也用于患者选择使用预先医疗决定, 预先安排自己在某些特定医疗情形下的医疗决策。
3患者自主权的法律保护
近40年来,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患者的自主权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实践中, 尊重患者自愿放弃治疗的决定,也逐渐被视为是尊重患者自主权的表现。在1976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自然死亡法》, 按照该法案,患者在临终阶段可以不使用生命维持设备来延缓死亡的来临,选择自然死亡。在1990年,美国颁布《患者自决法案》,该法案规定患者可以用预先医疗决定书来保护自己自愿放弃治疗的自主选择权。其后在1993年通过的《统一医疗决定法案》中统一规范了各个州的关于预先医疗决定的相关规定,弥补了实践中各州之间地域规范的差异和冲突。[10]《患者自决法案》和《统一医疗决定法案》这两部法案的宗旨都是保护患者的自主权,并且立足于以预先医疗决定的方式保护患者放弃治疗的自主选择。在2015年我国台湾地区颁布了患者自主权利相关规定, 这在亚洲是第一个旨在规范患者的医疗自主权的规定。该规定明确了医疗中以患者为主体,尊重患者的自主性, 保护患者的医疗自主权和保障患者选择善终的自主权益。其意义重大,在亚洲确立了专门规定来保护临终患者自主选择拒绝医疗和实现善终的权利。我国大陆目前在法律上虽然没有专门的患者权利法,但是对公民个体自主权的保护在法律层面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也是日益加强,值得关注。
3.1意定监护制度保护个人的自主权
所谓意定监护制度,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自己意思能力健全时预先选定自己的监护人,并且自我决定监护的设立和监护的内容等相关监护事项的监护制度。在法律上意定监护的效力优于法定监护。
意定监护制度的主旨内涵是尊重和保护个人在有意思能力时选择自己丧失意思能力后的监护人的权利,监护的内容包括人身照顾和财产管理等事宜。待本人丧失意思能力后,由其选择的监护人按照被监护人的意愿处理监护事宜。实践中意定监护是一个国家从法律上应对社会的老龄化,其宗旨是充分尊重老年人的自主性和老年人的自我决定权。最早的意定监护制度是美国弗吉尼亚州在1954年设立的持续性代理权制度,其后德国也参照此制度建立了照管制度,日本则在1999年通过《关于任意监护契约的法律》建立日本的任意监护制度。英国在2005年通过《意思能力法》修正和完善了其在1985设立的持续性代理权制度。意定监护比法定监护更尊重和保护个人的自主,平衡个人的个体独特性,尊重个人的自主意愿。让个人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以自我意愿来自主选任自己日后可能需要的监护人,可以说意定监护制度充分尊重了个人的意思自治和个人自主权。
意定监护制度在我国长久以来也一直是学理上探讨的热点问题。2013年修订后的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法律上突破了我国原有的监护制度,在立法上确立了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按照该法第26条的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自己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和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法承担监护责任。
2017年3月我国在对《民法通则》修订的基础上通过并公布了《民法总则》,并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民法总则》整体加强了对个人自主权的保护力度,第130条规定了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这是我国个人自主权法律保护的基础依据。另外,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民法总则》明确了意定监护制度,总则第33条规定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民法总则》把我国的意定监护制度扩展到了成年人,这将极大扩展了我国意定监护的实际应用。成年人在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可以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以及和监护人协商监护的相关事宜,以便在其丧失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相关事宜的监护职责。按照法律的规定,意定监护的监护人依法履行其监护职责,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果被监护人有一定能力尚可以独立处理一定事务,对于此类事务应由被监护人处理,监护人不得干涉。意定监护制度的设立体现了我国尊重个人自由意志和自主权利的立法趋势。
我国实践中已经有基于老年人意定监护制度的医疗救治授权书的实际应用。医疗救治授权书是老年人在身体状况尚可,神志尚清的时候,授权被授权人对自己日后神志不清,但需紧急救治时做出妥善救治方案的文书。医疗救治授权书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授权书,属于意定监护制度。从实质而言,这种授权也属于预先医疗决定的范畴。实践中一些公证机构也对类似的授权书进行公证,[11]以保证授权书的真实有效,也确保授权人的医疗意愿能够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使得授权的自主的医疗意愿能够在实践中实现。
3.2预指医疗代理的可行及其法律适用
意定监护就其法律本质而言属于法律上的代理关系。意定监护制度规定的通过事先协商确定监护人即是代理中的委托代理,要求以书面形式确定监护人的契约即是委托代理合同。具体授权监护的事宜等内容由被代理人也就是意定监护中的被监护人来决定。意定监护体现了对个人自主的强力保护。被监护人需要通过协商和监护候选人就监护关系达成一致,但是对于监护事务和具体事项内容的授权委托一定要被监护人自主决定。
基于我国民法总则已经确立了意定监护制度,在我国推行和使用预指医疗代理于法有据,是可行的。一个成年人可以在自己的亲属范围内或者亲属范围外自己认可的人中指定监护人,由监护人在日后自己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处理自己的相关事务,当然也包括代替自己做出医疗决定或者帮助自己落实自己预定的医疗意愿。在此有必要明确一点,基于意定监护旨在保护个人的自主权,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如果一个人已经指定了自己的监护人,但是又通过制定医疗救治授权书提前委托了自己在紧急医疗情况下、某些特殊医疗情形下的医疗代理人,那么针对这些情况下的医疗决定,医疗代理人的医疗决策应该优先于监护人。
3.3预指医疗代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我国目前的实践中,个人可以通过预先医疗决定这种提前嘱咐的形式来提前表达自己在日后紧急医疗情况、特殊医疗情况或者疾病终末期的医疗意愿。一个有意识能力的成年人不管以何种方式提前表达自己的医疗意愿都是可以的、也是合法的,但是在我国目前预先医疗决定书还不能被认为是生效的法律文件,即便是经过公证,也不当然就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其意义在于提前明确了个人的医疗意愿,希望在自己丧失意识能力时自己的意愿可以被知晓并能够被尊重和实现。实践中,患者病情危重时可能对患者产生不良后果和危险的检查与治疗都是属于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按照目前法律的相关规定,需要取得患者的书面知情同意,如果不能够取得患者本人的书面同意,则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因此,在实践中在患者病重昏迷丧失意识能力,处于不可逆转的临终状态时,是否采用生命支持设备或者是否撤除维生设备的决策从患者本人转移给了患者的近亲属。因此,在我国目前个人的预先医疗决定在其丧失意识能力后最终是否能够落实还需要取决于其近亲属的认可和支持。也就是仅仅立有预先医疗决定,那个人的自主医疗意愿能否得到实现在现实中还是不确定的。 基于此,为充分保障个人的医疗自主,可以通过移动监护制度事先委托一个人在自己丧失意识能力后落实自己的预先医疗决定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处理自己的医疗事务,可以预先委托自己的医疗代理人是保障自己的医疗意愿能够落实的有效途径,并且在现实中也是可行的。基于意定监护制度对个人自主权的支持和保护,在我国预指医疗代理是可行的,也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其实,我国实践中的医疗救治授权书就是预指医疗代理的形式。
3.4预指医疗代理人的条件
医疗委任代理人是指接受意愿人书面委任,在意愿人丧失意识能力时代理其表达医疗意愿的人。虽然充分信任是协商、选择和确定医疗代理人的前提,但是鉴于医疗代理事务是涉及一个人的医疗决策,医疗决策可以涉及有创医疗甚至关系生死,为保证代理人能够做出符合意愿表达人最佳利益的决定,在程序上应该格外严格。通常被指定的代理人都要求应当具备一定的法定条件。比如法国规定预指医疗代理人的资格需要医生的帮助判断;在美国各州要求在委托预指医疗代理人的时候必须要有见证人在场,并且代理人或见证人都不能与被代理人存在有任何利益冲突;我国台湾地区的病人自主权有关规定也对委托医疗代理人的资格和限制做了相应的规定,规定医疗委任代理必须是书面委托,委托的代理人应该是20周岁以上的完全行为能力人,并要求其书面同意。并且,该规定还限制了医疗委任代理人的范围,明确规定除了意愿人的继承人外,意愿人的受遗赠人、意愿人遗体或器官的指定受赠人和其他可能因意愿人死亡而获得利益的人都不得为医疗委任代理人。同时,病人自主权有关规定还对代理人的代理权限有明确的限制,规定了医疗代理的权限是听取医生的告知和代替签署知情同意书,依照病人预立医疗决定内容代理表达意愿。
为了更好地保护个人的自主权,不宜过多限制个人对代理人的选择。但是基于预立医疗代理的特殊性,为了更好保证医疗代理人能够做出符合患者最佳利益真实意愿的医疗决定,建议在实践中除了要符合一般代理人的法定条件外,预指医疗代理人还应该具备下列必要条件:①18周岁以上的完全行为能力人;②具备对医学常识的基本的认知和理解能力;③可以是患者的近亲属,也可以是患者近亲属以外的愿意担任其代理人的其他人。另外,还要特别对代理人的范围做出必要的限制,除了意愿人法定继承人之外,代理人不能够是因意愿人死亡而可能获得任何利益的人。并且在代理权限上要严格依照意愿人的授权代理医疗相关事宜,医疗代理的权限是听取医生的告知和代替签署知情同意书;依照患者预立的医疗决定内容代理表达意愿,做出符合患者真实意愿的医疗决定。鉴于医疗委托的重要性,预指医疗代理的委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委托医疗代理人时建议至少有一名见证人在场,该见证人必须与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都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如果被代理人有书写能力,应当自书,由被代理人亲笔书写、签名、填写日期。如果可以的话,建议进行公证。公证虽然不是必需的,也不能够增加代理的法律效力,但是公证机构的审查为代理符合相关规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避免由于委托不符合相关规定而导致无效。另外,医疗预指代理的终止也应是书面形式。个人可以随时书面解除医疗代理的委托,终止预指医疗代理。这也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自主的体现。
参考文献
[1]Kutner, Luis. The Living Will. A Proposal [J]. Indiana Law Journal, 1969,44(1):539-554.
[2]Lack P, Biller-Andorno N, Brauer S. Advance directives[M].Bertin:Springer, 2014.
[3]Brauer S, Biller-Andorno N, Andorno R. Country reports on advance directives[C]//ESF Exploratory Workshop Advance Directives: Towards a Coordinated European Perspective. 2008.
[4]孙也龙,郝澄波. 论新加坡《预先医疗指示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东南亚之窗, 2014 (1): 25-30.
[5]韦宝平,杨东升. 生前预嘱的法理阐释[J]. 金陵法律评论, 2013(2):5.
[6]郝新平.生前预嘱:生命归途的绿灯[N].中国医学论坛报,2009-6-18.
[7]Birchley G. Doctor? Who? Nurses, patient’s best interests and treatment withdrawal: when no doctor is available, should nurses withdraw treatment from patients?[J]. Nursing Philosophy, 2013, 14(2):96-108.
[8]何伦,施卫星.现代医学伦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
[9]Galambos C M. Preserving end-of-life autonomy: The patient self-determination act and the uniform health care decisions act[J]. Health & Social Work, 1998, 23(4): 275-281.
[10]Galambos C M. Preserving end-of-life autonomy: The patient self-determination act and the uniform health care decisions act[J]. Health & Social Work, 1998, 23(4): 275-281.
[11]周钢.意定监护上路,托付身体和尊严[N].快乐老人报,2017-5-29.